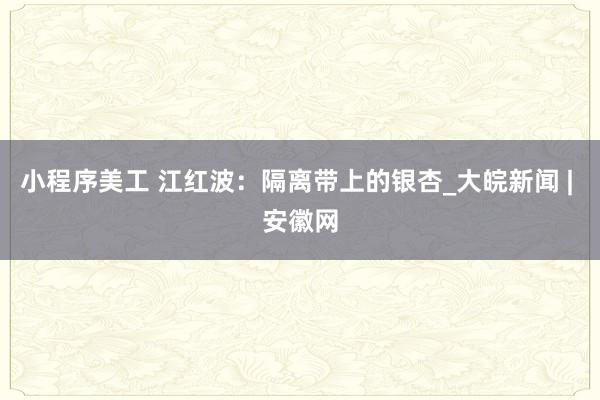
出门时间尚早,绕道紫霞桥去上班。在不慌不忙的年龄,在凉风习习的早晨小程序美工,走路是最好的。
远远地看见草坪那边的体育馆,又瞟了几眼足球场,谋生的单位就在马路对面出现了。这过境公路,车流来往奔走,我停下了脚步等它们过去。不经意间,看到隔离带草地上,一个个灰白或是金黄的果子,嗯,我奇怪地抬头:这隔离带上的银杏树,不知道什么时候结了果。它也不过茶杯粗细,一丈来高,树顶光秃秃的,不知何时被斫,还是风吹走的。
刘玉才/摄
这么小,还是个树孩子吧?银杏,也叫公孙树,爷爷栽下树,等到孙子才能吃到果实。山里的少年,零散的知识来自书本或是报纸。在老家的深山,漫山遍野的都是松树、杉树、毛竹和说不清楚名称的杂树。银杏树,这个称谓太书本。银杏叶在秋天,金黄灿烂,外形或是色泽,都像那小河里游动而自由的鸭脚,“啪嗒啪嗒”的,秋天就来了。村里人称为“鸭脚树”,那一颗颗的银杏果,是“鸭脚”。
装修最初印象中的银杏树,是跟着祖母去她的娘家走亲戚。在桃岭村口的半山腰,有一株古老的银杏,三五个人手拉手才能抱得住。凸起的老疙瘩,似影视剧里王府大门上的门钉,一个接一个的小程序美工,也不知道长了几百年。我从树下走过很多年,她就是只长叶不结果。
在距桃岭两三里的中店村,也有两株古老的银杏树,还有几棵香榧树,它们比赛一样粗过杀猪的木桶,高过房舍十多米,遮天蔽日。老银杏树似乎通人性,每年都结果。时节一到,晚风一吹,“簌簌”地落下来。路过的人都去捡。中店人看见也不作声,自然的风物,谁捡去了都是一样,何况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熟人。
老家的木桶里,白色的银杏、黄色的香榧,浸在里面。父亲说,这是把果子里的苦涩浸出来。隔三差五的,换水。就那样,一直到进入腊月,过年的花生瓜子开始炒的时候,父亲才拎着那银杏和香榧,到河里去清洗。香榧煮熟,炭火上烘焙;银杏沥干水分之后,直接下锅开炒。
“啪,啪……”银杏在锅里爆裂开来,果肉绿意盎然。父亲说,不能吃多,不许超过10个。每次就炒一小碗,大家抓几个过过嘴瘾就可以了。其实,也就两三碗银杏,详情页设计稍微有点空,年里炒炒就吃掉了。滚烫的银杏,在嘴里还是烫,嘻哈嘻哈地也就下肚了,糯糯的感觉,带着微苦。多年以后,看到开心果,嘀咕着,这不是小号的银杏嘛!
银杏,一年就吃那么几个,意犹未尽。物以稀为贵,我对那些高大的银杏树,多了几份仰慕。总觉得,不愧是公孙树,难得一见,难得一吃。
几年前,县城与开发区之间开大马路,理直气壮地从我赖以谋生的单位门口呼啸而过。隔离带上栽的绿化树居然全是银杏树,一车一车地拉过来,一棵接着一棵的,都是一丈多高,水杯粗细,一眼望不到边。瘦瘦的身影,是玉树临风,还是亭亭玉立,说不上。贫瘠的隔离带,树落脚少泥,活得很是艰辛。
岁月的风霜,炎炎的夏日,很多时候的路过,只是看看它们的存在。没料到,这秋风一吹,秋雨一淋,居然就一地的金果果了。带着白霜,带着秋意,我踮起脚尖轻轻捻一下,白色的银杏就露了出来,还是当年的容颜。地上的银杏,三个五个的,散落在隔离带的枯草上。
在这人来车往的马路上,看到这一树树的银杏,看到树下的果实,我站了片刻,路过的人挺多的,没有谁停下来去捡拾。我不知道,这些银杏在地上孤独了多久。树下低矮的灌木也在生长,给这繁忙的马路带来了片刻的安宁,只要你愿意停留下来,看它一眼。
一个人的心情,与他的生活经历有关,现在的人们都行色匆匆,没有多少时间停下。眼睛也大概不会被这路上的银杏所吸引,也不会想起银杏树有个昵称是公孙树。这银杏树,年纪轻轻就结果了,何况还很多,在这寒露时节,就那样赤裸裸地等着你。
每个人都有内心愉悦的东西,可能是生活经历各自不同吧?曾经留在童年少年的记忆,突然之间的相逢,那种欢欣小程序美工,如同我见到隔离带上的银杏时的心情一样。
特别声明:以上内容(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)来源于网络,不代表本网站立场。本网站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。如因作品内容、版权和其他问题需要同我们联系的,请联系我们及时处理。联系方式:451255985@qq.com,进行删除。Powered by 北京拼多多产品建模 @2013-2022 RSS地图 HTML地图
Copyright Powered by365建站 © 2023-2024 鄂ICP备2023020028号-1 武汉承致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版权所有
